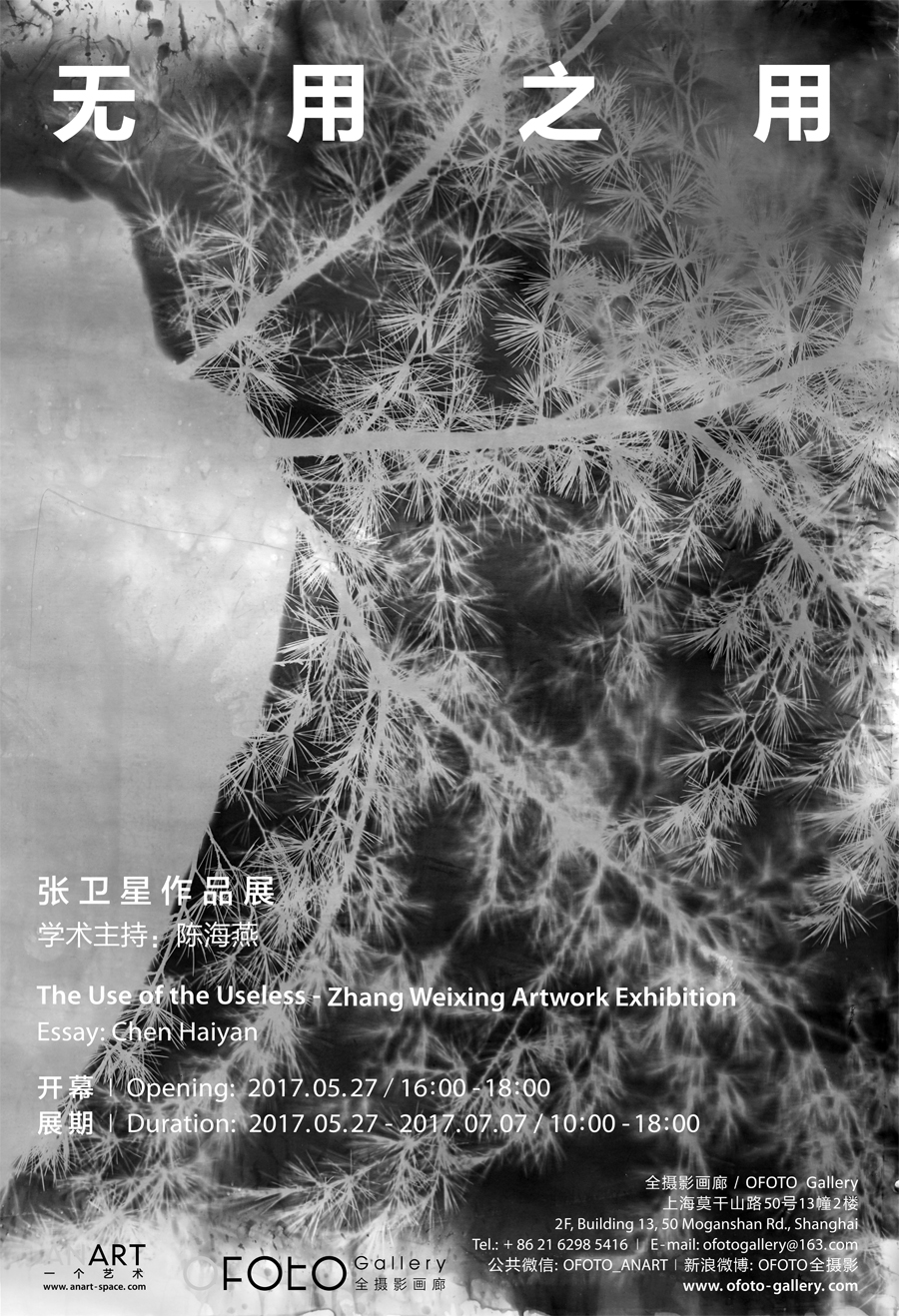无用之用
文:陈海燕
张卫星是个闲不住、好热闹的人,没事喜欢与朋友一起喝个小酒、划划拳(卫星猜枚狠有一手,尤其唱和起来,节奏音韵相当好听,号称“中原第二枚”),也是一个特别“哏”的人,争论起来,喜欢抬杠,人称“杠子头”。我曾有幸领教一回,所受所感乃用三字形容:“Oh,my God!”从某种角度来说,这样的人生动、有趣,且“好玩”。有意思的是,在艺术创作上卫星不像其他摄影艺术家那样,只单单固守拘泥于某一种语言方式去表达,而是喜欢动手尝试各类技艺,在实验、试验的状态下去激发并丰富他的创作。
诚然,在朋友们的眼里,卫星很像一个“拧巴”的玩家,哪里都喜欢去凑一凑、玩一玩,然后匠气十足地闭门鼓捣各类手工技艺,比如捏泥、烧陶、扎染、绘石、蓝晒、养蚕、写生……,并不理会外界如何评判。或许,每一次的乱象都是检验思维和激发灵感的好机会,因为无论怎样鼓捣,卫星痴迷于探索艺术的可能性却从未停止,而所谓做人做事的特立独行,最大的困难在于只要一点点的不坚持,就会被放弃。
博尔赫斯(Jorge Luis Borges)说过:“我的大半辈子都花在阅读、分析、写作(或者说试着让自己写作),以及享受上,我发现最后一项其实才是所有之中最重要的。”既然智者认可的享受,卫星也身体力行着享受自己玩儿的过程,那么我们也大可不必过于严肃和学术着去观看,而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“享受”并感受艺术。无论卫星用一贯自己擅长的物影手法再现自然景观,还是用自我习得的烧瓷技艺固化物事,都只是为了发现和表现寻常事物平庸状态下的质朴和不寻常,而之前一切状似“玩闹”的技术尝试和试验过程,最终成全为“无用”之下的有用。这几年,卫星大部分时间居留在河南嵩山,处在一种陶然自得的状态,做事全凭兴趣和兴起,且“见异思迁”,貌似一种自我放逐,遭人羡慕嫉妒恨。或许他脑海里那根创作的思弦,几近被调试得过于松懈,全然没有其他艺术家该有的紧绷,这使他的观看和思考一直处于玄览和悬想的发散层面,以致这些作品也少了表象的主线和体系。卫星尝试着用现实主义多头并叙的作品类型和呈现方式,捕捉这两年在嵩岳风土中所感受到的那无形无象、不可名状的某种天地间的氤氲之气,并牢牢扎根在中原的厚土之上。值得一提的是,卫星这些年还一直参与小朋友假期的训练营活动,辅导小朋友们“玩”摄影,也常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,并与他们玩得不亦乐乎,可谓某种意义上纯任自然的思无邪。
当下,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仍是主流思潮,胁迫并裹挟着几乎每个人的处世和做事原则。所幸,传统文化中还有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,尤以庄子的“无用之用,方为大用”可以断章取义加以对峙。这么看,卫星一贯持有的杠子头精神和自在玩艺术的过程,似乎有了另一种存在的精彩理由。套用美国画家惠斯勒(Whistle)说的:“艺术就这么发生了!”而卫星玩着玩着,作品和展览就这么发生了。
写于沪上
2017年4月27日